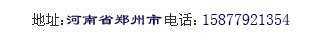本文作者是老编我的大学同学。在文革期间,大学停止招生。10年之后,我们有幸从陕西的四面八方汇聚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在我们班上,比我大八九岁的哥哥姐姐不少,比我小五六岁的弟弟妹妹也很多。慧敏应当算我的同龄人,但是她经历得更多,更艰辛。
-------------
十一小长假回队,登上黄土高塬,去找我插队时曾任教的黑池塬小学。
透过锁着有生锈的铁栅门,还能看到原大队部院子中间一圈花砖墙围着的一棵老松树依然枝叶茂盛。而隔壁的小学校却是一片静寂了。
七十年代的黑池塬小学是一个大院,院子里栽着不多的几棵树,左边有一片学农的田地,正对校门的有六间大砖窑洞作教室,教室门前有一个小院场,供学生集合站队。放得下一个班学生上体育。右边的一排窑洞是老师办公室也兼宿舍。我就住在一进在大门右手第一间办公室里,当年院子里摆着几个水泥乒乓球案子。没有操场,上操就到下面的场院。
这一切构成我早年教书生涯的场景,从这儿开始,除了三年多的省直机关行政工作和上大学的几年之外,我几乎教了一辈子书。小学中学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一个层次不拉地教过来了。教书最大的好处是教学相长,学生们逼着你学习学习再学习,以至于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教书使人心态年青,与学生少有代沟,最时髦的理念,最新的电子软件都知道,因为有学生的前卫,你也基本上不会太落伍。而我热爱的教育工作的起点就在这里,有一种回到大地原点的感觉。
早已荒废,与当年近两百人的热闹相比,只剩下满目绿色的植物,是树是草还是什么枝条,我没有仔细观察,虽然还能看到原来的教室已变成没有门窗的破窑洞,但却人迹少至,这里的午后静悄悄,不知成了谁家的草木林。八十年代乡村文明建设时,黑池塬是远近扬名的文明村,小学校有了新址,甚至还盖起了教学楼,但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计划生育和出生率下降打工族离乡,农村小学关停并转,黑池塬小学原来的窑洞教室和后来的教学楼均已成为历史。
没有学生娃娃的塬就立马就少了生气,在一长排两层楼的现村委会门口,我们见到两个穿戴整齐,操一口普通话的学生,大概是谁家的在城里读书的孙子。我们一行请他们帮我们照了合影后,我很认真地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里原来有个小学校,甚至我告诉他们我曾在这里当老师,心想说不定他们是我的学生的孩子或孙子,但两个孩子却一脸的茫然。
人常说“物是人非”,更何况物也没有了!从前有个塬,塬上有个小学,小学里有个知青女先生……也许不再有人讲给后代听,所有的一切,注定成为那年那月的一个摇曳在风里的传说。六十本命年,恍恍如隔世,梦中难知身是客,往事如昨,我们都已经成了黑池塬的观光人。归去不知来时路,遗失的仍然是一片关于青春的迷茫与梦幻般的记忆。
回忆总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过去发生的事,记忆试图还原曾经的客观事实,而回忆则赋事实于个体的色彩,知青有共同的集体记忆,但个体选择与贮存记忆的方式不同,心路不同,再现出来的回忆录则更丰富多彩,因为心理情绪具有超强的加工能力。如现在的我,隔着数十年的时空,去对生命中曾发生的故事再现和解读,此我非彼我,我会在两个我之间穿梭,生成第三个我。讲述一段过去的故事。
民办教师是一段特殊历史中,不列入国家正式编制的中小学教师。具有某种临时性,而知青可能也是一个临时性称谓,两个临时身份加一起,构成了我当年插队时的一段临时经历。
去大队当民办教师,有点歪打正着,却定位了我一辈子的职业。看过一部年拍摄的苏联红色经典影片《乡村女教师》,说的是一个叫瓦连卡的青年女性,从城市到落后且愚昧偏远的乡村做女教师,历经战争和个人的不幸,一次次与革命家丈夫分别直到永诀,却矢志不渝地投身于教育和农村孩子的启蒙,最终桃李满天下且获得了列宁勋章的故事。革命加浪漫是前苏联电影的基调,影响了50后一代人。那句经典的台词:“孩子们,你们要学会念书,写字,算算术。你们将要成为有智慧,有力量的人,我要使你们有理想。”或者曾鼓舞了我。我喜欢那种浪漫主义的革命理想,却不热血沸腾,因为革命离我比较远。
今天看来,当时做民办教师,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怎么当上的已经记不太清,大概是因为高中时是学习委员,学习较好,被同学举荐给队里的,方式应该与那个年代一样简单:或是说在队小学少了一个先生,好象是有一个前面插队知青招工回城了,新下乡的哪个学生学得好,去当个先生补个缺儿。刚下乡时就有人问过一回,我不想去,主要担心当了民办老师影响招工,招工出不来怎么办?那时可能我可能已经患上了一种文革传染病——人格分裂,一边说着要广阔天地炼红心,滚一身泥巴,长一手老茧,扎根农村干革命,一方面暗暗期待招工回城。
队里的劳动我比一般同学都不适应,下乡几年没学会用铁锨,搭不上膝,用不上腰。更不适应睡土炕,那时我们三个女生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不知那里来的那么多跳蚤。百度说:跳蚤属于蚤目的完全变态类节肢动物。小型、无翅,触角粗短。腹部宽大,有9节。后腿发达、粗壮。因而善于跳跃,能跳七、八寸高。跳蚤可以跳过它们身长倍的距离,相当于一个人跳过一个足球场。成虫通常生活在哺乳类动物身上,跳蚤跳上宿主后就不想离开,是寄生性昆虫,具刺吸式口器,雌雄均吸血;不知道为什么,那两个同学都没事,跳蚤光临只起个小红点,好象也不太爱咬她们。而对我情有独钟,且冤亲债主般纠缠!我被叮得滿身是包,痒得难忍,只能用手狂抓。可能是土炕也有湿气,我本是那种湿寒体质,那些包一抓就破,一破就流水,最后感染到全身几乎连成一片,用体无完肤一点也不夸张。衣服沾在身上一动就痛,要用水打湿了才能从身上将衣服揭下来……。好在最后终于找到解决的方法,是用花露水将睡衣的领口袖口脚下全封住,穿着袜子全副武装才能入睡。但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动辄上纲上线的年代,自己家里出身不好,用花露水是太小布尔乔亚了,自然躲躲藏藏。每天起床后将睡衣挂铁丝上远离地面,防止跳蚤偷袭,还得把自己好好用毛巾擦一遍,怕被人闻出来,塬上那时又缺水,纠结无比。
生活上也比较难适应,后来被派下公社去修红星水库,住在塬下的李家沟大队。主要的活是装土和推架子车,一般是男的驾辕,女的推车。其他同学是越累越能吃,而我是越累越吃不动,以至于推着架子车身子发飘。这一次又动员我上塬教书时,我就从水库的体力劳动中当逃兵了。
看到我在那儿吗?第二排,左数第二位。
开始是顶替某老师,没有津贴,可能也有试试看的意思,后来大概是看我还是个教书的料,就有津贴了,民办老师挣了全工分,还有一月七八块钱的津贴,一下子觉得经济上独立了,而一般知青下乡家里都是要贴补的。
七十年代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孩子们都不好好读书,老师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虽然也上语文课,但好象没有上过数学课,主要教副课,音乐和美术体育。学校就我一个女先生,孩子们顽皮不听话,也有点欺负女老师,受文革中武的影响,男老师对不听话的学生,边哄带吓唬,有时候耳光或脚就上去了。我那时候不敢也不喜欢那样对学生,但是高嗓门大声训斥学生的时候也还是有的。记得一个叫万军的学生,相当有个性。上课打架怎么也劝不住,我连拉带扯地将他同那个被打同学分开,推出教室罚站,不记得是不是也拉了他耳朵。后来他把大字报贴到我门上,只六个字:先生拉我耳朵!以示抗议。
上语文课,学生喜欢听我绘声绘色读课文如讲故事,可能是我的普通话还算标准(与当地人比),也比较会和学生互动。上音乐课就领着学生唱《小松树》之类的革命儿童歌曲。学生对我比较亲近,可能也有对城里人的好奇,身后总跟着几条小尾巴,类似于现在粉丝。甚至我多年后见到一个学生在城里工作相当有成就的学生,竟用我的名字打个颠倒改成了她的名字。
那时农村学校上课简单,我们学生多,没有复式班。常听得一个教算术的老师领读黑板:
1+2=3,1+2=3——
2+5=7,2+5=7——
都往牌(黑板)上看,都往牌上看——
谁不往牌上看,叫他站起来。谁不往牌上看,叫他站起来——
稚嫩的童声跟在一个带着几分方言的普通话后面,拉着长腔一声声地在校园里回响,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教学法,当时忍住不敢笑出来,今天想起却充满了温馨。
夏收时我常常白天领着学生拾麦子,一边寻找需要表扬的好人好事和写通讯的资料,晚上回来加班写稿子,写好的稿子,要刻成蜡版,连夜油印出《三夏战报》再发到地里。不知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在队没有专门的文书,我就临时顶差,帮大队写个材料报个奖什么的。遇到母亲住院不得已时我就带着三四岁的小弟跟我下农村,他后来老跟别人说他也插过队。我上课就给他一本连环画儿,坐在教室后面自己玩儿,当个旁听生,或者就托付给村里有玩伴的熟人,那时人那么质朴,竟无人提意见。
那所塬上的小学校,那个背似乎永远也直不起来的不苟言笑的老校长,总戴着一顶退了色的蓝帽子,帽沿是软软的拉不平的那种,但一双眉眼却有神,他不象校长,却象个老校工,整天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将学生搞乱的东西一一归置好。他少言却不怒自威,学生都怕他。学校没有灶,他吃派饭,轮流在村民家里用餐,他每每从派饭人家带回稀罕的吃食,象对小孩子一样地给我留着,只是恓惶娃儿离开城市来到乡下插队。
王老校长的房子总是晚上的最好的聊天室,他炉子上的茶一年四季都烧着,但是他话不多,倒象一个开茶馆的掌柜,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好去处。村里的干部们以及有点头脸的人晚饭后总聚在这里说古论今。我记得来的最多的是矿长,秋月的父亲,一脸的严肃,那是一个年轻时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后来一直是大队的矿长,可能是属于改革开放前就有了的农民企业家,我却以为他大约是黑池塬上“最后的乡绅”。他不但总为村的工作出谋划策,也有一套治家教子密术,是塬上少有的八个孩子个个出息的父亲。秋月的哥哥夏利是我学校的同事,不管夏利和我们聊得多开心,只要他父亲一来,必定住口,成了一个只当听众的好孩子,家规之严可见一斑。另有个开大拖拉机的司机也是王校长的常客,拉粮食的时候,他总喜欢用中山服的大口袋装满满一兜儿豆子,放在学校的铁炉子上烤出诱人的香气……
我则一边织毛衣一边听他们聊天,我的所谓贫下中农再教育,乡村文化的熏染多是这样听来的。后来才知道乡村文化是分层的,乡村的上流与底层在文化上也存在差异。乡村的上流社会由各色能人构成,虽然经过文革,但好象我当时没看出有谁象造反起家的乡霸。
有时来了下乡的女干部,与大队一墙之隔的小学校,就成为临时招待所,加一张床住在我那间窑洞,就成了室友,由此也认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这些人在当时很使我长见识。
记得那时学校比较多的活动是片上(几个学校一起)或公社的文艺汇演和学校开运动会。当地老师都有家,放学后忙活农事。我却无家无事,带了运动队和宣传队,出去汇演完全是自编自导的节目,无非是唱歌舞蹈对口词三句半几种简单的文艺形式。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胆,什么都敢上。但没有统一的服装是一个遗憾,我就和学生们商量,各家出钱统一宣传队服。记得那时统一的是白衬衣,男孩子天蓝色短裤,女孩子红花裙子,那时候社会上是不穿裙子的,但我不知为什么就是是坚持做裙子,记得当时精打细算,生怕多花孩子们一分钱,大布料套裁。缝纫机线都是我在家里拿的,几毛钱一尺布,还要布票,一个孩子只需要交三块多线五六尺布票,我自己借农民的缝纫机全部免费加工。
因母亲曾在被服厂做裁剪,我上学前就敢站着脚踩缝纫机用下脚料做沙包发给小朋友。后来她带班授徒,文革不上课,我也跟着剪剪做做,但布太金贵,常有不得手的痒痒。总记得姥姥的教侮:艺不压身,下乡拿农民的布当纸练,在当地做衣服算是小有名气,那时只用一把剪刀,没有软尺,用线绳在身上一拉,甚至用手一咋,就能八九不离十,常常被叫到农民家中去做衣服,一小时能做出两条裤子来。给孩子做衣服,家长当然很高兴,一群孩子们穿上统一的服装相当亮眼,记得那时没有化妆材料,红纸印泥火柴棒全部作过尝试。出去汇演抱得奖状归来大家皆大欢喜。我也似乎很有点成就感。
没有体育器材,就因陋就简。跳远没有沙坑,让同学们在地边挖掘个坑,把土挖虚了,练习急行跳远。没有跳高架子就让让两个学生拉一条绳子让学生学跳高。门前的一条大路,用皮尺拉出六十米,撒上石灰,就是跑道。现在想想一点不科学,学生受伤怎么办?早上一群男老师看着我在操场中间带操,一点也不觉得奇怪。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敢干!
不种地的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放学后和学生打打乒乓球,更有时间练习写字。镇文化馆的燕乐天老师那时教我在一大碗水里放几滴墨汁,在硬土铺成的脚地上练习书法,哈哈!那是最早的地书呵!那地真有宣纸的感觉,每天毛笔上挂一串铜钱,蹴下悬腕地书,用尽一碗水。可惜他没教我选个帖好好临,或者说了,我不以为意,虽然花了不少功夫,长进不大。上大学时迷上古文字,临甲骨文金文拓片,也习小篆。还参加过学生书法比赛,得过小奖,玩得就是插队时那一点点功夫。再后来太忙乱,心不净,临帖没了耐心,终也没有学出来。书法一直是野路子,后来也就慢慢荒疏了,或者退休后会再捡起来也说不定。
有一段还被选入公社的故事队,故事队有好几个原来的同学,大家经常疯作一团,喜笑颜开,全公社塬上到处转转讲故事。这个不打怵,因为教师注定了是个口力劳动者,自嘲为“卖口条”的。陕西方言讲故事,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当时却不知为什么,后来学了《古音韵学》方知关中秦语是上古中古时代的官方普通话。方言里可作知识考古的内容太多。当时只对故事中那些歇后语和当地方言里的幽默语素极感兴趣。什么“癞蛤蟆过门槛——又墩勾子又伤脸!”,“屎巴牛支桌子——尽力而为呢!”“筷子里拔旗杆——没高的!”“屎壳郎坐轮船——臭名远扬”。你问他红白喜事帮人忙啥呢?明明是主事,他却告你说:“打狗支桌子,吆鸡关后门,引客人娃巴屎!”那种不动声色的冷幽默,相对今天上课时的一本正经,故弄玄虚,有太多的真实。今天回味起来,仍觉深不可测,博大精深。
记得镇文化馆有一个知青美术小组,一群黄堡知青美术爱好者集中起来画画,当时画得最好的是回乡青年存锁,他后来被推荐上了美术学院,毕业后回到铜川师范教过一阵书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他的母校车站小学,一辈子愿作黄堡人。当时的指导老师就有著名画家耿健,我那时有一幅水粉习作,号为晨曦,画一个老奶奶天蒙蒙亮,带着小孙女去给加了一夜班的青年突击队送早餐。他很认真地帮我改了数笔,画面马上活了起来,诚惶诚恐,崇拜极了耿老师,学画很有动力,有一阵子,每周都从塬上下到黄堡街上的文化馆去画画儿。当时素描水粉都学过一点点,但那个活动没有持续多久,七六年最后一级工农兵学员,公社有意推荐我去考美院,虽然说好社来社去,为能上大学和画画,我也很乐意,很快填了初审表,由于当时我父亲是右派,又在三反一打中右倾翻案,问题一直没结论。当年的美院没有可教子女(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子女,但可以教育好)名额,第一关政审就被刷了下来。对于画画,似乎是一个梦随之破灭。上大学时还画几笔,后来要读的书太多,工作家务两头忙,也不再怎么画画,前几年有点空闲,心血来潮,又去老年大学学国画,学了一段,感觉好象也不是那么回事,又没时间练习,只好又一次搁笔。
非吃专业饭者,书画乃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主要是用来陶冶情操,闭门修心,六根不净者难为!那时能一天天关在家里画画写字,心自是比较静的,后来风风火火,忙乱于俗务,雅兴不存也是必然。
前几年我回到塬上来,拜见当年小学校的同事,大家一聚,这些同事过得都不错,民办老师的身份早已转成公办,他们拿着退休教师工资享受农民的自由,土地和宅院。风水轮流转,该是我这个大学老师羡慕嫉妒进行时了。
这次回队,只见到我的两个学生,丽萍和百娃。但知道有几个孩子后来考上大学,干得不错。丽萍是因嫁在了本队,一辈子留在塬上。当年可是漂亮机灵的一个小姑娘,宣传队的台柱子,而且热心。我到小学校教书时离开了知青大灶,拿一个小煤油炉子做饭,做稀饭下面还凑合,但不能蒸镆,她自告奋勇说:“老师!让我妈帮你烙镆。”一开始不可收,一来二去,成了她家的常客,几年都吃她妈的烙镆。往往是带走一点面,拿回来更多的镆,碰了知青点没粮了开不了灶,也会有同学从庙背后过来混馍吃。我刚大学毕业时,丽萍还来找过我,现如今,五十多岁的丽萍有三个儿子,几个孙子,塬上没有了小学,孙子不能象丽萍当年在家门口读书了。她说村子的娃少了,有的进了城,有的只能下黄堡车站小学去上学,她孙子属于后者,为了陪读,她在李家沟村租了房子。陪读是一个难差事,每周回来还要管拖了一周的家务事。百娃则在城里包工程,不但在城里买了房,还在塬上收拾了一院好地方。冬天享受城里的暖气,其它季节则尽享乡下的清新的空气。
我拉着我当年的学生丽萍的手,她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这是我的学生百娃,是一个有经营头脑的人。
再次告别已不存在的小学校,那里承载着我过多的记忆。
对于小学教育,我没有仔细考虑,当时只是做了一阵娃娃头,哄着孩子们高兴自己也乐,谈不上教育理念和方法。但是今天中国的教育问题多多,破解一定要从最初级的小学教育甚至幼儿园开始。曾遇到几个台湾教育界的朋友,他们对台湾教育也多有忧虑,其理想是退休后去幼儿园打义工,以便从根本上修理教育。我不敢有这样的宏愿,在大陆推动某种教育理念谈何容易,但我或者会找一处山青水秀的小学校去支教,再过一把当娃娃头的瘾!
上一篇:
慧敏|知青的岁月,落荒的记忆
赞赏
人赞赏
中科医院专家微信白癜风治疗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