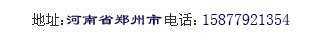一年前,我们的“乒乓林”里,插进一棵柳。
柳姓得好,细长个,一米八十多,一看就是运动员的料。株说,柳是台湾来的。于是顿觉有些遥远,有些陌生。柳操着华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一见面就带来一种甘蔗的气息。
几乎与此同时,樟也来了。樟是上世纪市青少体校的球员,直拍。如果说,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直拍进攻,那么,柳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横拍正反两面弧圈。
柳第一次亮相很优雅。他柳树般飘逸的身材,令我自惭形秽。他的服装和装备也令我不敢面对。他背一个很大的乒乓球专用包,黑色的,绣着英文“butterfly”(蝴蝶)。他一进门,先向我们鞠躬,再跟我们一一握手,十足的绅士风度。接着,他打开黑色蝴蝶包,拿出清洁剂、胶水、底板、胶皮……一边操作,一边介绍说,这是美国清洁剂、德国胶水、日本底板、日本胶皮。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他白皙的手指很灵巧,先用清洁剂把胶皮洗干净,再上胶水。在等候胶水挥发的时候,他说我去换衣服。
乒乓球原来可以这样文雅!柳给我上了第一课。
那一刻,我贪婪地闻着胶水的香蕉味,看柳的胶皮在灯下闪光。然后,我想我自己的丑陋。我是五短身材;我的拍子是老式的颗粒胶皮,面粒都已经老化,像祖母脚上的老茧;我没有运动服装,裤子是平脚裤,上面是和尚领汗衫;我也没有柳那样的运动包,乒乓拍和臭袜子,都塞在那只永远油亮的挎包里……正想着,更衣后的柳进来了。他白皙颀长的身体,配上雪青色的“蝴蝶”短袖衫,短裤也是“蝴蝶”的,那双专用的乒乓鞋上,也飞着一对蝴蝶的翅膀!一望而知,他就是运动林中的那棵白柳。
柳利索地粘好拍子,上场打球。他臂长力大,两面弧圈像挥舞着两把大刀。这刀切般的弧圈球,速度飞快,稍一怠慢,就在台上不见了踪影。最了不起的是,他强拉弧圈球的落点几乎都在边线附近。那激光般精准的落点,令我发出阵阵惊呼。我呆呆地看着柳。他的脚步是漂亮的探戈。在灯光下可以看到,他极为干净的拍子上打上一个个尘土的球印。这尘土的印,在我眼里也是漂亮的。
他这天走后,株介绍说,柳是台湾名手,跟蒋澎龙一起打过球;毕业于辅仁大学,来大陆前在一家外国语学校任体育部主任兼乒乓球教练。
我肃然起敬。我看过蒋澎龙的球,那是什么水平?曾经排在世界前几位的!柳与他同道,即使偶尔陪练,也是高手了!
后来我们就叫他柳先生,小心翼翼的。也交过手,差距太大了。跟他打球,就像罗圈腿跟飞毛腿赛跑一样,内心充满了自卑。胜了他一局,简直引为奇迹。柳一如既往地谦恭。每打完一盘,总是主动走过来跟你握手,没有一点胜利的骄矜。
渐渐的,就熟悉了。也一道喝酒,一道开玩笑。原来柳独立着,未婚;父亲让他离开台湾来上海,说是跟一个朋友联手在上海搞实业,而且是十几亿的大实业,正缺少高管。可柳来了后才发现,父亲说的其实只是海市蜃楼。他一脚踏空,只好开始在上海自谋生路。
柳是在台湾见过世面的人,却在上海屋檐下低了头。他先后给过我三张名片,一是广告公司业务经理,二是印务公司业务经理,还有一张,我忘了是什么公司,但也是经理。可见他换工作之多,择业的苦。他说自己是跑业务的,按业务量取酬。我暗暗为他担忧:这些行当竞争何等激烈,上海人都视为畏途,您柳先生人生地不熟的,吃得了这口饭吗?
果然,柳一次次辞职。他埋怨时有句口头禅“上海难缠”。后来,他连支付出租车费都成了负担。偶尔,他也带几个年轻人来打球,似乎当着教练的样子。我想,这才是您的本行,愿您顺畅。
柳依然来打球,次数却少了。最令我惋惜的是,他不再那么优雅,不再一次次地使用清洁剂,撕胶皮、粘胶皮。他的脸色也憔悴了,头发稀疏起来,还见了白发。他一遍遍地跟我说,“上海难缠”。
他的球速不知怎的,也慢了。我们的比分,倒渐渐接近起来。我不觉得这是我们的球在进步。柳说话少了,沉思却多了,有时局间坐着也走神,不知在想什么。他打球不再那么潇洒,那么舒展。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他是骑着助动车来的。这使我吃惊。在上海,有几个台湾人会以助动车为交通工具?而他,在我心目中又如此不凡!
这以后,打赢他不再是奇迹。樟赢过他,株赢过他,杞赢过他,我也赢过他。但我们赢得并不愉快,因为柳的笑容越来越少。这不是我们打球的本意。
三月的一天,凄风苦雨。
我下午三时许走进乒乓室,却见柳还在吃饭,他吃的是盒饭,很少的菜,很少的饭,但不知怎么的,很烫,冒着很多热气。他吃得满头大汗。
我说:“您慢慢吃,吃完了休息一下,我们打一盘。”
他看看我,不作声,目光有些怪。
我坐在他身边换鞋袜,听他把饭吃得很香。我看见有一件雨衣扔在一边,就想着一个台湾年轻人,骑着助动车在上海风雨中跋涉的身影。
吃完了,柳才说:“我不是来打球的。”
我惊问:“那您是……”
柳说:“我是来告别的。我要走了。”
我说:“回台湾?”
柳说:“最终要回台湾。”
我问:“为什么要走?”
柳说:“上海难缠。说出来您不相信,我每月收入只有二三百元,吃饭都成问题。我在台湾月薪有四万多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一万零七百元。我后悔不该轻信我父亲的话,随便就浪费了一年。”
我说:“但我们认识了。”
柳说:“是啊,只有这点是值得的。”
他把那件雪青色的短袖衫留给株,把一套阿迪达斯留给我。他说还要跑几个地方,把打球的装备一一送给上海的朋友。
他跟我握手,不再因为打球。然后他披上雨衣,走进电梯时他说:“欢迎你们到台湾来打球。”
那一天我若有所失,球一次次打飞。虽然我知道,不是我们的林子里容不下柳。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乒乓球毕竟是奢侈品,它必须依附于生活。
那一对蝴蝶的翅膀,现在飞在株的背脊上。看见这对翅膀,我就想起柳的长脚和探戈般的步法。柳消失以后,我们的林子一下子矮去了许多。
乒乓从来都给我们欢乐。但柳的离去令我察觉:乒乓原来也会忧伤。
年第4期《收获》长篇小说-王城如海(徐则臣)长篇连载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中篇小说橙红银白(旧海棠)子非鱼(彭瑞高)六十岁的中文系女教授(汪若)短篇小说枪手(韩少功)大湖(周嘉宁)远水无痕看电影记(翟永明)夜短梦长只要你上了火车(毛尖)明亮的星吉狄马加:返回古勒布特的道路(耿占春)吉狄马加的诗(吉狄马加)《收获》函套珍藏版1,北京治白癜风哪家好治癜风